
性
这无疑是人类最有意思的一个话题,我说的有意思不是指它本身,而是指我们对它的态度。像讨论中午想吃什么一样讨论性取向;像讨论餐桌礼仪一样讨论性行为;像讨论喜欢左手用筷子还是右手用筷子一样讨论性器官——你敢吗? 时至今日,我们已经很难有足够的耐心去直观性的本质,性被裹上了一层又一层的文化外壳,它的面目被修饰的面目全非。如果剖开这个文化外壳,你会发现性不过就是一种自然的生理活动,我们作为一个物种靠着性活动繁衍壮大。从这个角度讲,性活动跟我们打喷嚏、吃饭、放屁、排泄好像没有什么本质区别,都是维持生存、发展物种的手段而已。性器官跟我们的鼻子、嘴、肛门等器官相比,也不应该有太特殊的地位——从职能上来讲,它既不崇高,也不卑下。 但是有了文明之后,我们就像吃了禁果的亚当、夏娃一样,突然意识到有些生活习惯虽然是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,但却是“不文明”的。既然不能废除它们,那就用遮羞布掩盖它,让它在暗地里进行,使它尽量少地出现在文明人的视野中(或者说,至少在我们扮演文明人的时刻,不要提起这些不雅的事情,以提醒我们仍然是动物这一尴尬的角色)。 
文明人要不要谈论性呢?当然要谈论,不谈论性,就说明还有一块区域是文明没有征服的。为了消除掉这最后的耻辱,文明早就对性展开了所谓科学的研究,只是这研究总给人以大张旗鼓、虚张声势的感觉。而且研究来研究去,我们甚至都已经不太清楚他应该属于哪个领域了,它既属于生物学、心理学,又属于社会学、政治学甚至法学、伦理学。 这一方面体现出性话题的复杂性和多维性,另一方面体现出科学研究方法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尴尬处境。不过相比于以前的避而不谈,我们现在至少已经开始谈论它了,但是我还是不满意。一件事情真正被谈论不应该是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被谈论,那是“研究”不是谈论,研究是把对象放在试验台上,去围观,去指点,然后把它放回培养皿。而真正的谈论应该是在日常语言中给他一个位置,让它进入我们的生活世界。我们不是在围观它,而是在用语言将它整合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,它跟我们的衣、食、住、行一样成为生活中的一员,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提到它,而不用过分顾及周围的环境。 不管是什么事物,在我们给它一个寻常眼光之前,再精确的研究都是含糊其辞、避重就轻。 但是,“性”这个话题缺乏的恰恰是这种“寻常”态度,要么讳莫如深,避而不谈;要么吊儿郎当,戏谑调侃;要么一本正经、严肃探讨——总之,直到现在,我们还没有学会像谈论一个寻常之物一样去注视性、谈论性,总是在闪烁其词。 我们把这种对生殖器与性活动的暧昧态度称为“生殖器谬误”。 在这样谬误前提下,我们很难期望关于它有一套健康的伦理与法律规范。 可以举一些极浅显的例子来说明,关于性的一些荒谬态度。 
一、性取向中国的记载不是很明了,但在古希腊,我们可以确信,城邦的公民们都有非常自由、多元的性取向,有条件的男性公民既可以娶妻生子,同时也可以选择一名少年做自己的伴侣。对这位少年而言,这个男子既是人生导师,也是情人,它们的关系是受到社会认可和容许的。 同性恋在希腊受到了最大程度的宽容——它被理解为一种行为、一种倾向,而不是一个群体、一个标签。在古希腊人看来,就像有人喜欢吃酸的、有人喜欢吃辣的一样,性取向也只是一种个人倾向而已,完全没有必要为此大惊小怪,其中并不存在道德上的高下之分,它们也更不会想到要因此而惩罚谁。 但是随着文明的更深入发展,道德观念和公共舆论将权力的触角延伸到私生活的每个领域,性生活开始被管制,管制的第一步就是对性取向划出所谓合法与非法的界限,将其变成政治管制的阵地。 直到现在,在很多人眼里,同性恋或者是邪恶的,或者是病态的——要么将其看作道德污点,要么将其看作生理倒错——总之,同性恋是一个不该出现的东西,一定是哪里出了错才会出现的怪胎。我们要么谴责它,要么矫正它,因为它是不合理、不健康的。 正因为它是以“不合理”的姿态出现在这样一个理性世界,所以我们产生了一系列的歧视态度。 
性学研究越来越表明,每个人都有双性恋的倾向,只是一部分人对异性的取向更明显,一部分人对同性的取向更明显,而还有一部分人对两种性别都怀有相同的热情。从这个角度来讲,异性恋、双性恋和同性恋在性取向光谱上只有度的区别。就像我们无法将具体多少粒米定义为“一堆”一样,谁也没有足够的权威将某些人定义为“同性恋”。 但事实却是,为了更好地攻击同性恋,我们已经将其做成一个帽子扣在某些人头上,而且再也摘不下来。同性恋由一种先天的、或隐或显的倾向,变成了一群人固有的恶劣属性。 更重要的是,这会使我们忽视一点:只有当他们行使性行为时,他们“同性恋”的帽子才有意义。但是这些人并不只有性生活,他们有自己的职业、爱好、公民权等等,但他们无论多么认真生活,我们还是只用这一“特殊”的性取向来定义他们。这是对这些人作为多样性生存者的粗暴否定,这就是一种暴政。 
二、自慰长久以来,我们一直认为只有以生殖为目的的性行为才是有意义的、也就是合法的性行为,除此之外都是不堪启齿的。实施自慰行为相当于承认和放纵自己的性欲,不仅向欲望投降,被欲望俘虏,而且以这样一种见不得人的方式去迁就欲望,这是一种猥琐的行为,一种恶心而危险的行为。 我至今还记得曾有一个15岁的大男孩,对我声泪俱下的“忏悔”:他刚刚无师自通地学会了自慰,觉得非常舒服,他很喜欢“做那件事”,但是心中的恐惧和焦虑却还是日重一日。他觉得自己和以前不一样了,和身边的同学不一样了——他学会了一件邪恶的事情,这件邪恶的事情也使他变得不再单纯,这甚至成为他告别少年阶段的分水岭——那个纯真的少年再也回不去了——他变“脏”了。 饿了要吃饭,渴了要喝水。我们很轻易地会原谅一个饥饿的人狼吞虎咽的不雅,甚至会觉得一个汗流浃背的人牛饮的样子看着很爽。自慰难道不是对先天欲望的一种排解吗?为什么会在自慰的同时会心怀愧疚甚至悔恨呢? 自慰行为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他人,我们的愧疚是针对谁的呢? 针对自己?是担心自己“精尽人亡”吗?科学研究早就表明,科学的自慰不仅不会损伤身体,而且会帮助我们放松身心。李银河有句话说的好:“如果说自慰会引起什么精神损害的话,那也是由于社会对自慰的严厉压制和谴责所引发的内心冲突和恐惧。” 就算自慰真的有害健康,在我看来这也是一件私事,只是一个关乎健康而非道德的私事。我们可以关切地劝说当事人,但断无指责他的权利。自慰的人也不应该有愧疚的感觉,就算有也不应该是道德层面的愧疚,而只应该是宣称减肥的女生忍不住吃了一块蛋糕的那种愧疚。 
说到这里,我又想起一个人,小时候学校里有一个非常儒雅的老师,谈吐不凡,举止高雅,是学校的年级主任,班里的男生女生都很喜欢这个老师。但是很快我们便从高年级学生那里打听到一则轶事:他曾经在另一所更大的学校官至副校长,年轻有为,前途光明,但是有一天同事去宿舍找他玩(以前的学校,教师宿舍就在校内),发现门没关严,推门撞见他在宿舍里***色录像自慰。从此他就被冠以“流氓”的称号,官职一降再降,单位换了一个又一个,再无前途可言。 我现在还能回忆起,这位老师在我们心里的形象是如何崩塌的:他不再是一个谦谦君子,而是一个道貌岸然的流氓、一个淫棍,一个危险的、猥琐的人物。他越是温文尔雅,我们越是嫌恶他、甚至害怕他。我当时的想法是:这么危险的一个人物,为什么还让他留在学校呢?为什么不抓起来呢? 现在我当然知道,应该惩罚的不是他,而是那个不打招呼推门而入的同事。惭愧之余,我想的问题是:为什么他会有如此的境遇? 自慰的人并没有伤害任何人,我们为什么要嫌恶他?他只是做了一件几乎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,只是在做的时候被发现了而已。于是他就不得不承受鄙夷的眼神,被冠以流氓的称号。 与上面对同性恋的暴政一样,对自慰行为和自慰者的态度也是一种暴政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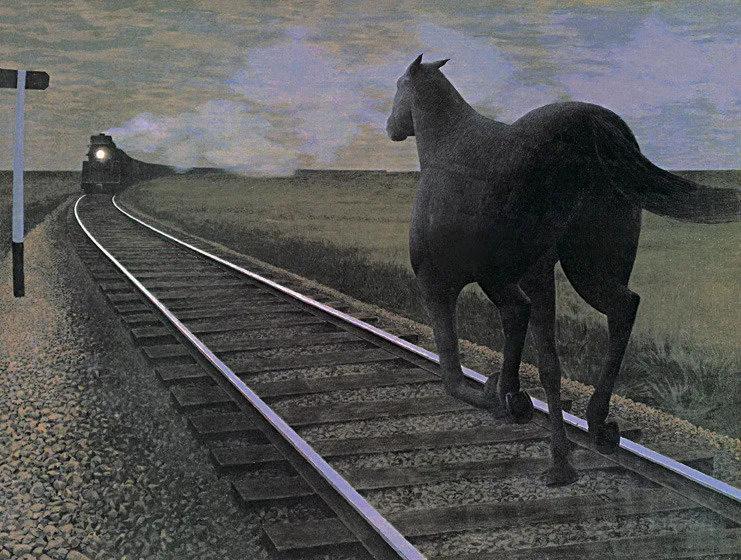
三、婚前性行为性当然会涉及到生育,但毕竟这二者是两码事,可仍然有很多人将它们混为一谈。 生育虽然是两个人性活动的结果,可是一旦孩子出生,就会涉及到很多公共的家族问题、社会问题,这就又不是两个人的事了。初生的孩子要想得到社会的认可,获得其存在于世的合法性,首先其父母的性活动必须具有合法性,而性活动的合法性又来自于婚姻。 于是婚前性行为就受到了阻击。 婚姻就是一场仪式,通过这场仪式,特定两个人的性活动获得了合法地位,他们性活动的产物——孩子,自然也将获得认可。甚至直到现在,婚姻也起到这个门槛的作用,未婚少女和少男在门外,与其说他们从属于社会,不如说他们从属于各自的家庭,他们受到家庭的庇护和遮掩,社会并没有给他们肩头放太多的责任和负担。要想真正成为一个社会人,深刻而全面地参与社会生活,你就必须结婚,作为另一个家庭的主人去接受社会的清查、管理与其赋予你的期待与责任。恋人是私人关系,而夫妻是公共关系。它们的不同并不体现在二人的感情上,而体现在社会角色上。而这一切都始于婚姻——婚姻是每个社会正式成员的加冕礼。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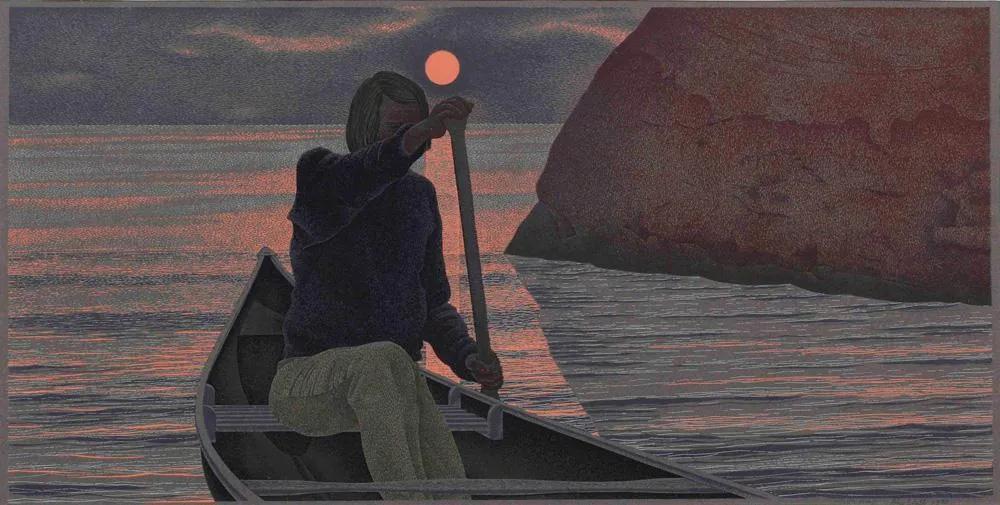
正如上述所说,其错误之处正在于:我们将性活动与生育混为一谈了。 在古代社会,人们并不清楚生育的奥秘,搞不清怎样才能成功受孕,怎样才能不受孕,所以混为一谈可以理解。但是随着生理知识的增长和避孕技术的提高,我们早已能做到只享受性快感而不怀孕,如果还对婚前性行为大加讨伐,就显得很不合时宜了。 其实,正如自慰一样,只要性活动没有妨碍或者伤害到其他人,那么谁也没有权利去说三道四、指指点点。罗素就曾经大胆提出婚前性行为不仅不应禁止,而且应当鼓励——“就像买房子前要先看房一样”。 虽然性器官作为身体的一部分,是每个人的所有物,我们似乎理所当然地掌握对它们的支配权。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,社会早就规定好了它的使用范围、使用方式甚至使用场景、使用频次。 这是为什么呢? 是担心性活动会妨碍别人吗?这个理由太牵强,因为有很多是没有妨碍别人的。是担心会搅乱社会秩序吗?谁也无法拿出确切的证据表明婚前性行为、自慰或同性恋能在多大程度上浮动人心,有多大可能导致社会万劫不复。 性自由当然会和很多卫生、健康和遗腹子的问题相关,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它所解决的那些问题。 其实只要有稍微理性的思考,你会发现,对传统性道德的固守在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。以前囿于知识的局限,我们必须以道德来规范我们的行为,以确保健康和秩序,但是现在,我们通过技术同样可以解决这些问题。 现代生活中所包含的最根本的伦理原则就是“自由”。而“性政治”作为身体政治中的重要一类,就是要将性纳入政治和法律的规范内,纳入到社会的品评中。这其实是与自由的原则相违背的——性政治正在面临自身合法性的问题,面临它与自由的紧张关系的问题。 
其实自由的性态度很简单,我们在上面也反复提到: 作为一种身体行动,性活动当然应该受到规范和管理,但是应该将管理限制在最低的、仅仅是必要的限度,这个限度就是只要经过当事人同意、不直接损害他人的利益、不为社会增添负担(比如怀孕),就不该受到干涉,哪怕是谴责也不行。 有人会说,同性恋当然损害我的利益了,它污染了我的眼睛、破坏了我对人类未来的美好向往。 先不说这类理由本身所具有的模糊性和自以为是,人类历史中堕入专制与独裁的阶段,无一不是从这些理由为起点的。 况且“危害社会风俗”、“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”这类借口,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先入为主的意见,那就是“这件事是错的”。但是请注意,我们现在探讨的不是对错的问题,而是个人权利的问题,这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领域。吸烟或许是错的,但这是人家的权利,只要一个成年人愿意吸烟并能够在正确场景下吸烟,旁人是无权置喙的。 甚至于,我们不仅不应该以自己的好恶为少数性活动编排欲加之罪,而且倒应该反过来追查那些所谓的义正词严的讨伐者,以问他们个“妨碍隐私”的罪名。
|